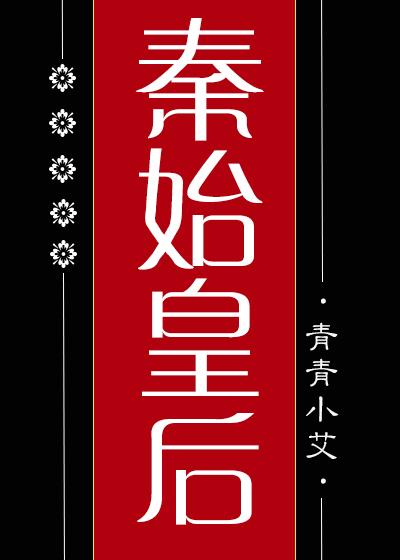千千小说>清平调里浣溪沙 > 第80章(第1页)
第80章(第1页)
一袭明艳的红纱做外衣,里面若隐若现搭配了浅粉的肚兜,头上的发髻看似随意地一挽,几缕发丝从耳鬓处随着风摇曳。粉面上一双丹凤眼四处留情,游扫到眼前的三人时,那双丹凤眼定了定神,一抹惊色跃然。
浣溪向两名琵琶女道:“两位姑娘辛苦了,我们想单独同潇泓姑娘处一处。”
两位琵琶对视一眼,识趣地退了出去。
纯画满目凄然,先开了口:“雀儿,你还认识我吗?”
雀儿眼神暗淡了下去:“这么多年,小姐的容貌并没有大变,自然是认识的。不过,你现在来找我,怕是黄尘覆绿水,往事不复了。”
纯画不解:“你甘心堕落在这绣春楼吗?”
“堕落?!”雀儿冷笑一声:“你是富商家的大小姐,你可知,这两个字我这等贱命都不配有。我当回京是一道云梯,可以帮我改头换面;却不知,是另一道深渊。哈哈,我无人疼,无人爱,唯一心念我的人都死了,我活着,还要为着什么贞洁牌坊吗?千人踩万人踢,这痛,你这个千金大小姐又怎么能悟得,哈哈。”
纯画眼角已经溢出了清泪,滚在覆面的黄沙上,滚出了一道道泥印子:“你跟我走吧,我们还像以前不好吗?一切还来得及。”
雀儿冷然一笑:“回不去了!你走你的阳关道,我走我的堕落桥。就让我没心没肺活着吧,对我来说,现在挺好的。”
“雀儿,你不要任性了好吗?我赎你出去”
纯画的声音近乎哀求了。
雀儿神色一凛:“出去?出去继续做你的丫鬟吗?哈哈,我现在可是名满京都的花魁娘子,要快活有快活,要金钱有金钱,我用得着你赎我出去吗?哈哈,收起你那迂腐的仁义道德吧,你那套东西,在生计面前根本不值一提。”
纯画的泪水夺眶而出,险些歪倒在地。不知是因为雀儿的遭遇,还是她那道心底的防线,被狠狠得冲击,没了抵御的力量。
浣溪赶紧抱住纯画的头:“不关你的事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,你救不了所有人。潇泓姑娘不是小孩子了,她会为自己筹划的。”
见纯画稍微平复了下。浣溪起身,与雀儿对视,先是施了一礼,然后道:“潇泓姑娘,多有打扰了。我们几人本是好心,担心姑娘是被迫,所以想方设法前来救援。不过,如今姑娘已在绣春楼立住脚跟,我们也会顺从姑娘的意愿,只是若需我等相助,还请姑娘直言。纯画姐姐在京都初来乍到,第一想念的便是姑娘了。”
六年,当初在济州浣府并不出挑的雀儿如今长开了,容貌昳丽,早已不是当初随在纯画身后唯唯诺诺的小姑娘了。
雀儿微微一笑:“刚才,是潇泓冒犯了,还请各位不要介怀。还请纯画小姐记下,以后只有潇泓,没有雀儿。当年救助的恩情和小姐的照拂,潇泓会永记在心的。过往如烟云,若小姐们不嫌弃,我们重新交个朋友吧。”
浣沙拍掌:“好,重新交朋友。”
纯画却木讷着,并未答话。
浣溪笑道:“自然是愿意和花魁娘子相交的。下月锦绣工坊于京都开业,还请潇泓姑娘过去捧场。”说罢,从怀里掏出一封礼帖。
“说来惭愧,工坊开业,并没有什么拿的出手的节目,还请潇泓”
未及她说完,潇泓便扬了扬首,笑道:“这个好办!绣春楼编排歌舞最擅长不过了,交给我便是。”
浣溪感激地点点头,还不忘提醒句:“羽织楼的事,不妨碍吧?”
潇泓叹了口气:“上官磬的事因我而起,但罪不在我。他已经伏法,两不相欠了。我只能说往事如烟,不去提他了。”
红颜入京门
几人从绣春楼出来,各怀心事。
纯画眼角的泪还在簌簌地流,整个人都抽噎着。浣溪挽住她的臂:“纯画姐姐不要哭啦,她自己觉得好便好吧,若她哪天想回头,不是还有我们接着吗?”
纯画凝神,缓缓道出一句:“溪儿,我先前学的,是不是都是错的?”
浣溪挠了挠头,叹了口气,旋即停了脚步:“不,姐姐,你学的那些都没有错。橘生南方为橘橘生北方为枳,你学的东西对你是有益的。因为你是世家小姐,你是富绅千金,你是万众耀目的中心。”
“那雀儿呢,雀儿的选择有没有错?”
浣溪蹙眉:“我也不知道。她自己选的路,外人不可评价。她一出生便出生在阴暗处,父亲入狱,母亲自尽,自己成为婢女。本以为父亲出狱后一切都会好转,却是另一个深坑。被典为妾,被发卖绣春楼。在这之前,她无路可选。你先前所学的,她又如何受用?”
纯画抽噎着,将将缓了口气:“随她去吧。若是当初不让她回京就好了。”
世事无常,福祸相依,若是不让她回京,也难保雀儿不怨怼她。你总想着行事没有差错,可事件本就繁复纷扰,哪有什么绝对的对与错?
“咳咳”,浣沙故意咳嗽了一声:“若是明日和今日天气一般才好,适合出行。”
明日事棱儿到来的日子,浣溪和纯画才从雀儿的事情中回过神来。浣溪说:“明日,得安排人去城门处接一下溪儿才好。”
谁去合适呢?城门道远,军兵把守,把守城门之将是皇城司潘誉天。
“你们别看我啊,我不去?”浣沙在一边叉着腰,嘟着嘴,斜睨着一侧。
浣溪嘻嘻笑着:“小浣大人难道是公务繁忙?”
浣沙赶紧道:“不忙!”
“若是不忙的话,就你啦!劳烦小浣大人了!”浣溪眨了眨眼,笑说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