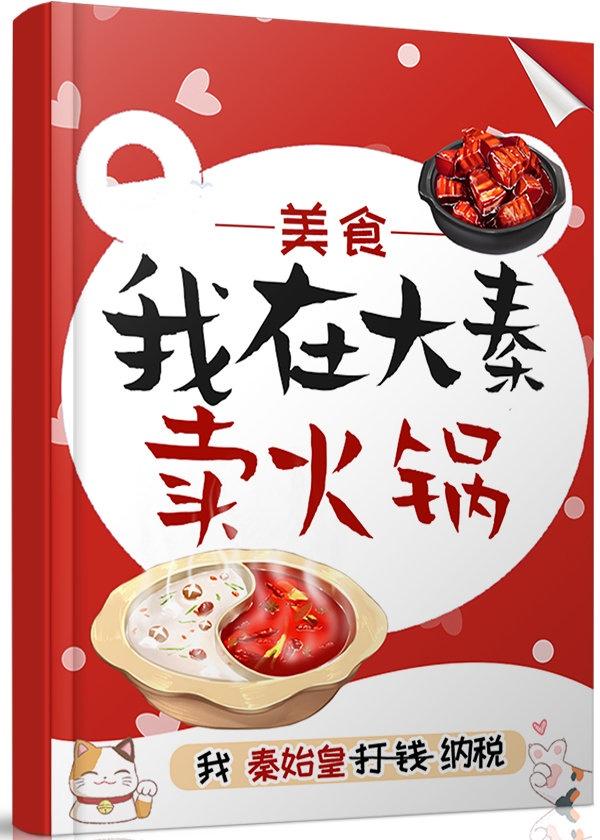千千小说>SD短篇同人(主bl向) > 第88章(第1页)
第88章(第1页)
再到周末三井来找他,他特地拿白布盖在正画的那副架子上。他想三井一定会掀开来看。
三井偏东拉西扯不肯去看,拉着他出去约会,吃了饭又去看电影,看完电影又去打游戏机,打完游戏机已是深夜,他拉着他泡酒吧泡到淩晨两点歌手都下班了开始放散场的轻音乐。
铁男简直憋不住,三井怎麽能忍住不问?他都开始起稿了,花了好多天才让他满意。他还想惊豔三井一把。
直到天边放亮最后的私密项目结束,三井才环着铁男,叫他别睡,一起去画室,他要在太阳升起时欣赏他的肖像。
——完—20230319——
番外(六)夏至
上午9点,太阳还藏在地平线之下,遥远天边刚有些微红的早霞。
三井寿已经在窗口溜达3小时了,该死的生物钟,让他在坐了差不多四十个小时的飞机之后,从天空漆黑可惜有云不怎麽能看得到星星一直等到了现在,仍然不困。
前提是他之前在头等舱里睡得昏天黑地。
在沙发上刚打了盹的铁男哈欠连连地瘫着,懒洋洋道:“让你坐船,偏不干。现在家里的时间是晚上9点,一会儿吃了早饭,你就该困了。”
“谁家好人9点睡觉!”三井寿不顺心思,嘴里没好气,“无论早晚!喂,出门逛逛啊,呆不住了。”
“今天大风,你看外面的树。”那些摇晃着稀疏的枯黄叶子的乔木被风吹弯了腰,“现在零下好几度,至少等太阳出来,吃了早饭暖和点儿吧。”
三井寿挑着一边眉毛斜视铁男,似笑非笑地哼道:“给你个机会再说一遍。”
铁男立刻从沙发上跳起来,头也不回地往身上套衣服,“现在出发!”
这类无聊的斗嘴也不知重複过多少遍,也不知如何开始,也不知何时厌倦。日子仿佛没有尽头,又似乎卡在了某一个片段。
也许这就是三井寿坚持要来乌斯怀亚的原因吧,一个被称为“世界尽头”的距离南极最近的城市。
城市和城市不一样。工业城市像憨厚老实给一把草料就满足的耕牛,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;政治中心像五彩斑斓的鹦鹉,不止模样迷人还能说会道;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像熊猫,捕猎的本领都被卖萌掩盖了;而乌斯怀亚这样的小城,像小飞象章鱼,偷偷藏在人迹罕至之处无人问津,直到某个偶然的曝光,一下子就成了时尚单品,似乎不在梦想清单里提上一笔便算不得是个有閑有钱有品位的人了。
好歹也算文艺类工作者的三井寿也在惦念着乌斯怀亚。但他自认并非流俗,他的念想源于一支歌,他逛街时候偶然听见了很上口的两句,“直到世界尽头,也不愿与你分离,曾在千万个夜晚许下心愿”。当时他忙着去赴约,没听完,回家之后专门找出来,越听越觉得心有灵犀。
“你说,世界有尽头吗?”他裹着沖锋衣迎着风,漫步于异国他乡清早无人的小镇街头。街路边堆着莹白的残雪,绵延到莹白的山尖尖上,连接天边那堆莹白的梦。也许云彩的去处就是雪的尽头。
铁男穿三井同款沖锋衣,少见地将拉链拉到了下巴,他一年有364天敞着穿外套,今天是地365天。“地球是个球。球没有开始和结束。”
“拜托,你应该是浪漫主义者。一会儿我们坐船去看世界尽头的灯塔。”
“如果不刮大风。现在我现实主义。”铁男因为懒惰而煞风景了。再说,浪漫主义是什麽好词吗?铁男挺了挺胸膛,风太硬,刺得疼,他又缩起肩膀,主要表达一个能屈能伸。真想念湘南海岸啊……围炉烤肉来一壶酒最幸福……退一万步,有空调的酒店房间也可以。
风不仅大,还冷。这个季节,家里该有三十几度,而这个从前无人问津突然间因地理位置而火热了起来的世界角落,物理温度在零下。
空旷街上无人的早晨,三面围着雪白的安第斯山脉,嗅着潮湿腥鹹的海风,他们俩像一对企鹅宝宝,不小心遗失了繁华世间,幸而彼此能贴在一起取暖。
三井寿张嘴,呛了一口风,咳嗽几声才说出话:“现实主义者先解决眼下问题。擡头,前面有家店。”
没见过太阳没出来就开门的南美店铺,你当在新京呢,24小时有吃有玩有人伺候着。铁男一顿腹诽,然而擡头,前方二十几米的路边还真有一家亮着灯的海鲜店。门脸涂成海洋蓝,招牌上画了一只巨大的橙红色帝王蟹,爪子伸到二楼房檐。店名不认识,一串字母,不像英文。
“长见识了!”铁男惊到。
三井挑眉而笑,“我就说该出门了!我再猜不错!”
“三井,你运气是真好!”话音未落,铁男向前跑了两大步,堪堪躲开三井的高踢腿。接着他快速向海鲜店走去,听见身后跺得嘭嘭响的脚步声,嘴角拉到耳朵根。
海鲜店果然只有一位看店的年轻人,听见门响,擡头瞪着走进来的这两张东方面孔跟见了鬼一样。
三井先笑,试着讲英文,“你好。我们想吃点儿热乎东西,太冷了。”
店家的英文口音很重,本来英文就很烂的铁男一句也听不懂,只能看着三井寿,跟着他走到窗边落座,等店家去后厨才问他们聊了什麽。
“哦,他说他父亲出海了,因为风浪太大,他担心父亲,睡不着,才会这麽早开店。他去给咱俩做早餐,说如果有空可以下午再来,父亲回来的话,店里会上新鲜海鲜,这个季节多半有帝王蟹,特别甜。”
“那游船回来,咱俩再来试试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