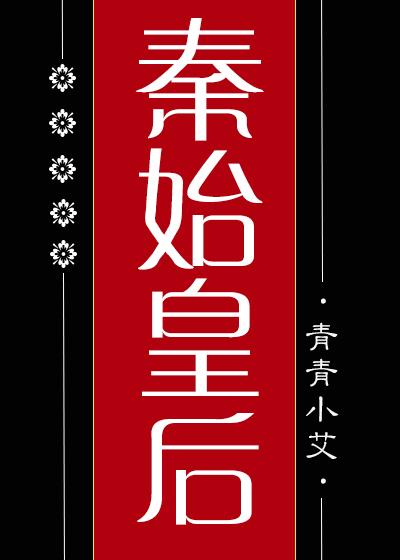千千小说>悬刀池野 > 第420章(第1页)
第420章(第1页)
“犹豫了许久,孙澄音执意如此,便也派工匠着手去做了,只是尚未完工。”呼延臻说着,伸手摘下言栀发梢草梗,“你想去看看吗?去看看像不像他。”
“好,”言栀几乎脱口而出,“我想去的。”
“明日便去吧。”呼延臻想来他定是心急难耐,便擅自主张,“那我们且早些回去,用了膳,泡个汤洗洗尘,明早我来找你。”
言栀答应了,回去的路变得漫长,他心不在焉吃完了晚膳,侍女为他洗净了长发,待他沐浴更衣,回到房中躺在榻上,只留一盏幽暗的灯。
之前的每晚,江潜也会盯着屋顶发呆吗?
言栀躺在与他同样的位置,终于拿出那张揉皱信件,瞧着满纸的“言栀”。
这个写的焦躁,是他在心烦吗?想到自己还会心猿意马吗?又划掉了,工整重新落笔,是因他的珍重吗?他是很爱我的吗?
这里滴落两点墨,洇开了。
这麽多的“吾妻亲啓”,夜夜沾笔濡墨,为何又停笔踌躇了,只一遍遍书写名讳聊寄思念?
言栀想不明白,他从始至终都不明白江潜的爱意,他的一举一动,他的神情他的话。
但当重新抚平信件安放胸口,为何心又是抽痛不止?这是爱意吗?
但为何爱要摧心剖肝方才罢休呢?
花山
言栀一夜未眠,直到拂晓微光,细雪濛濛,停歇后出了日头,橙黄蔓延至脚跟。叩门三两声,是极其微弱的。
他能听见门外人蹑手蹑脚摸上了锁头,略施力门便应声而开。
言栀没有锁门,只是一夜虚掩着,见呼延臻来,他哑笑着发出“嗯嗯”声响。
呼延臻来到他榻前低诉:“若是累了,明日、后日倒也无妨”他撚起言栀落榻垂下的发丝,方才触碰,后者便一个激灵坐直了身。唯余呼延臻的手干干立在空中。
“我要去、我要去的。”笑容从言栀脸庞消散,他对镜自照,匆忙整理衣冠。呼延臻暗叹一气,见他手上慌乱,执起木梳替他理顺。
“好了,”呼延臻放下木梳,拍拍言栀肩头,“我带你去。”
不远不近的路,呼延臻见言栀在草原上如长草般随风披拂,摇摇欲坠,便摆手遣退牵马的侍人,吩咐手下套车。
一夜未眠,言栀头还刺痛着,时不时恍惚,却极力使自己显得自然,却发现神思如同杯中清水摇晃不止。
“上车吧,”呼延臻抿了抿唇,先一步登车,“累了就靠着我睡,路很长,睡一觉刚刚好。”
马夫听他这般说道,心中也有了杆秤,执缰的手微微松了。
言栀坐在马车上闭目养神,却又时时瞧向窗外,不舍得轻易睡下。这条路没準江潜走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