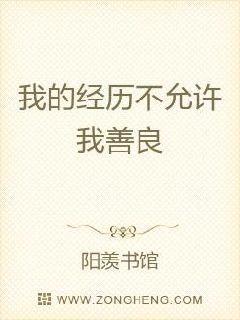千千小说>封神之清平游记 > 第1206章 故人(第1页)
第1206章 故人(第1页)
“太后,臣冤枉啊!”年希维一把鼻涕一把泪,“军工院一直有人私下与藩镇做生意,贩卖武器装备甚至技术,在镐京不是什么秘密,陛下也知道,只是不好查。我得到确切消息,段凝等人也在做买卖,这次就是往藩镇运输物资和装备,目的地是上宁府,还附上了大致的清单。我大概看了看运输机的数量,上去查看后,自己估算,除了物资、装备对不上,数量与清单应该没有多大出入,谁知道会是运往西线和水师,臣真是冤枉。”
“你从哪里来的消息?”
“不、不知道。”年希维不敢看咬牙切齿的窦太后,吓得脑袋一缩。时间太紧,他也没有时间去查证。
“不知道?!”窦太后腾得跳了起来,一拐杖敲在刚才被打的地方,痛得年希维一声惨叫,“你这个混账东西、白痴,消息来源都不清楚,冒冒失失就去拦截中军府运输的物资、装备,我看别说一部尚书,你个狗东西做个县令也不合格,咱们家怎会有你这种姻亲,简直丢我们窦家的脸。黎萱,把这条老狗给我抬出去,扔在外边,别管他死活。”
黎萱劝了好半天,窦太后才消了气。又打电话让年家派人入宫来接,将年希维抬上车,送去医署疗养。
气消后,窦太后一个人坐在书房里,联系权武:“武儿,和你说个事……年希维这个白痴被人算计,得罪了中军府、右军府和北齐水师,差点被权谨罢免,我看要保他继续做尚书,非得花大力气不可。你觉得这个事是不是权中纪或权谨的反击,借机清除咱们娘俩在朝廷的人。”
“娘,暂时不好说,我先综合一下京兆府的情报,分析分析,再和娘商量。”
“你们讨论吧,娘会吩咐那些人别冒冒失失乱动,谁再敢背着我们出手,坏我大事,我打死他。”
年希维向天守布武和刑部供出了举报信息的来源,查过去的时候,提供信息给他的人已经死了多时,就是他跳脚查物资、装备的夜里喝药自杀身亡,一看就是早有准备。
……
“什长。”走进营房,丁虫达立正向张财富报道。
“头,你别这样,我可受不起。”张财富连连摆手。他刚升任什长不久,上头将老上级丁虫达调到他这里,让他头疼不已。
“我的伍长呢,不介绍给我认识一下?”丁虫达将被褥和装备卸下来,放在一张空床上,扫视着营房里的人。
“我哪里有什么伍长,还指望你老帮帮我呢。”
正准备收拾铺床的丁虫达一愣,转身坐在床边:“我听说新任了万红林在你手底下做伍长,怎么没有?他可是连续立了几次功,你可别瞧不起人。”
“万红林是你老带出来的兵,又是上头任命,我怎会瞧不起。”张财富嘿嘿一笑,搓着手走到他面前站着,“这不巧了,他在芙蓉县受了伤,被派去雄鹰岭学习,顺便养伤,我现在一个伍长也没有,问了上头,说现在没有合适人选,让我自己看着办,要不……委屈你老先帮我带几天?”
他其实明白上面的意思,别看丁虫达被贬,直接撸为兵士,不过敲打敲打,不出意外,应该很快就会升回去,给他留了一个伍长名额,一看就是给丁留着,代理几天就可以转正。
“行,先带带。”丁虫达也不客气,他有这个底气,你们什长都是跟着我混出来,要是不听话,当初我怎么教他,现在就怎么教你们,“还有,别叫我头,还有什么你老、你老的,什长就是什长,兵士就是兵士,坏了规矩不好。”
“那我叫你丁叔得了。”张财富说着,又让那些兵士过来,“叫丁叔。”
众兵士叫了后,丁虫达将他拉到外边,道:“上头有任务交代下来,明儿带着大家出去一趟,告诉他们,从现在开始,所有人不许吃东西,只允许喝少量水。”
……
“大哥,今夜在唐郡休息,明日就可以到扶风郡。”仲钦乘伸手指了指窗外的大酒店,司机将车停了下来,他与仲钦丞走下车,吩咐司机和护卫去停车,兄弟二人往酒店里面走。
到门口的时候,几个一看就是有身份地位的人从里面笑谈着走出来。兄弟二人未免在藩镇的地头惹事,退到一旁,等他们先走。
其中一位看起来四五十岁的人打量着兄弟俩,走了两步,突然回头道:“冒昧问一下二位小兄弟,你们可是姓仲?”
“晚辈正是姓仲,不知先生有什么吩咐?”仲钦丞抱拳道。
“没什么,看错了人,不好意思。”中年人笑了笑,又看了二人两眼,和其他人说说笑笑走了。
“莫名其妙嘛。”仲钦乘嘀咕了一句,二人进入酒店,定了房间,去电梯的时候,见仲钦丞皱眉沉思,“大哥,你该不会还在想那个小老头之事吧?他不是说看错了人。”
“看错了人会问我们是不是姓仲,世上有这么巧的事?”仲钦丞横了他一眼。
二人默默无言,到了楼层进入房间后,用仪器检查了一遍,将门反锁,仲钦乘坐到兄长对面,道:“我们出京到扶风郡办事,镐京很多人都知道,传到藩镇也不是不可能,大哥觉得有人想害我们?”
“小心驶得万年船,尤其是在藩镇的地盘上,更是大意不得。”仲钦丞给护卫发了信息。
“不如联系清平子,让他派人来接我们,反正也不远,大不了连夜赶路。”
“别忘了老头子的吩咐,我们自己过去,和他们派人来接意义不一样。江陵府的人马上到扶风郡,不能坏事,再看看吧,情况不对再说。”
“不会吧?如果梁王这么小气,派贺晋到扶风郡恭贺是为了我们兄弟俩,简直笑掉人的大牙。我们算什么东西,无权无职的纨绔子弟罢了,至于嘛。”
“你觉得穆明裕为何提议我们兄弟来扶风郡考察?因为我们是户部尚书之子,是伍相一方的人,他们或许想借机确定什么。”
“我觉得没那么复杂,不就是想恶心恶心老头子,万一咱们兄弟俩不小心在路上被哪个不长眼的藩镇做掉,就可以耻笑老头子好几年。朝堂上的争斗,三岁小孩似的,看起来高深莫测,说穿了就是学前班打架的水平,想起来就好笑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