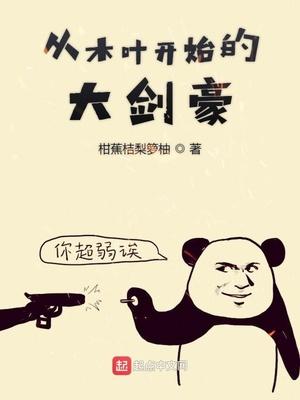千千小说>穿成荒年女县令,带家国走向繁荣 > 第387章 余九思收贿(第1页)
第387章 余九思收贿(第1页)
银票张张相叠,自下而上看去,竟是数不清有几多。且这样的“银票小山”,还不止一座。余九思指尖发麻,他在心中不断告诫自己,做戏要做全套。所以他选择了伸手上前,夹起了一张银票于指缝之中。宁顺佑见状,嘴角露出一抹满意的微笑,不禁在心中嗤笑。这小子声势浩大的进城,又是堵城门,又是抓他的人,做给谁看的?还不是做给百姓和他这个知府看的。眼下这小子如愿分得银子,便与他宁顺佑是一条绳上的蚂蚱,想跑都跑不掉了。他的目光只在托盘上停留片刻后,便火速移开了目光。无他。这么大笔银子,已经是他此次获利的三成了,还是有些令人心疼的。余九思看着宁顺佑神色变幻,垂眸掩住怒气,接过托盘自顾自地数起了银票。他数好后,宁顺佑唤管家取来了木箱,将银票通通放了进去。箱盖一闭,似是一间暗无天日的牢笼,扣住了无数百姓的血肉在其中。“宁知府的手下混是混账了些,但您方才说得对,您的人,自是该交由您来处置,不好假以人手。”余九思拿起木箱起身,为难道:“但方才跟在本将身后的,是巡抚大人手下的兵,他与本将一同进城,将城门口的冲突看了个十成十。所以眼下,本将暂且不能放人,还望宁知府理解。”宁顺佑闻言险些破口大骂。什么意思?他好话也说了,银票也给了,到头来这小子还要拉出巡抚大人来压他?他的语气染上了一丝咬牙切齿:“那郎将何时能放人?”余九思轻笑,“宁知府莫急,不过是做做样子罢了。本将将人押上两日,再将城门关上两日,待巡抚大人问起,也好交差才是。”关城门?!宁顺佑注意力完全被这三个字所吸引。他立即反对道:“不行,城门今日就得开,不能关。城门紧闭不开,表示城中必有大事发生,郎将,您莫要害本官啊,若是上面问起,本官如何交差?”余九思朝他摇了摇头,说了个囫囵话:“若这本就不是本将的意思呢?”宁顺佑双眼猛然睁大。不是他的意思,那就是上面的意思?!他惊疑不已,看向余九思,伸手指了指天上。余九思不说是,也不说不是,只是说:“宁知府也莫要让本将为难,两日后,本将放人、开城门。咱们互让一步,都莫让对方为难。”宁顺佑怕都要怕死了。他在心中思忖,余九思口中的“上面”,到底是哪上面。是巡抚?是朝中各部?还是天子?他心中惊疑不定,好在余九思收了银票,稍微安了安他那颗怦怦乱跳的心。余九思走后,管家上前给宁顺佑斟了盏茶,不解问道:“大人,那位郎将到底是谁手底下的人?”宁顺佑皱眉摇头,“不知。他此次来得太过突然,一点风声都没有。”管家看着门外,阴恻恻道:“若不是他突然前来,还将本该滞在路上的货船救了出来,您也不会损失那一大笔银票。”“啪——”宁顺佑抬手给了他一耳光,“什么货船?什么银票?”管家心下一紧,“噗通”跪倒在地。“大人恕罪,老奴年迈头昏,口不择言。老奴老眼昏花,将吃食看成了银票!”宁顺佑眉目低沉,说话意有所指:“记住了。洪是禄州府泄的,与我昌南府毫无关系,他禄州府不分青红皂白泄洪,拦了我昌南府的赈灾粮,本官没找他们算账算是好的了。至于粮商所卖粮食,也是他们千辛万苦运过来的,作价几何,本官无从干涉。谁问,都是如此!谁来查,都是如此!”其实禄州府的闸口是如何开放的,他与管家心中门清。但只要有人问,闸口,就是禄州府所为。他们昌南府,就是实打实的受害者!宁顺佑面上的狠厉还未褪去,“至于他是谁的人”他说到这儿一愣,回想起余九思那句“跟在本将身后的,是巡抚大人的兵。”不禁豁然开朗。卢巡抚的身影从他脑中闪过,他喃喃道:“是他的人?”他突然哈哈大笑起来,神情莫测:“看来咱们的巡抚大人养的狗,也不太忠诚嘛,谁给个肉包子,就跟谁走。枉他还想提携这小子,将这大好机会给了出去。”宁顺佑确定了余九思的阵营,心情大好,不禁话多了起来:“若是他不收‘赔礼’,也不道来路,或许还需要本官费神去防。但此子终归是年轻,目光短浅了些,心神摇摆不定,易受惑。”管家有意讨好他,跪着上前赞道:“大人英明!能在大人手下讨食吃,是奴才天大的福气!”宁顺佑一声哼,“利字动人心,这天下没有永恒的阵营。”管家连连称是,他似是想到了什么,突然问道:“大人,那些粮商这两日没办法出城,且今日来了一队肥商,他们带有不少粮食,这”宁顺佑皱了皱眉。无论朝廷如何派粮赈灾,粮食在昌南府都是有销路的。毕竟今年刚过秋收时刻,昌南府的百姓家中却毫无存粮,至少接下来一年都要买粮吃。若是将那些粮商遣送回去不行。宁顺佑的心口在滴血。他手指轻敲椅子扶手,片刻后说道:“卖完粮的,先让他们在城中稍候两日,两日后安排他们出城。至于那刚来的”他顿了顿,咬牙道:“让他们稍安勿躁,这两日切莫有所动作,待本官再探探那小子口风再说。”“大人英明!”管家马匹重拍。余九思出了宁府后,站在巷尾看着前面正忙活的薛迈。习武之人五感本就灵敏,不过片刻薛迈便感受到了他的目光。他放下手中活计,对府衙之人说道:“我去尿尿,劳你先看着,数量切莫出错。”:()穿成荒年女县令,带家国走向繁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