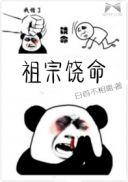千千小说>家国旧情,爱连环,恨连环 > 第406章(第1页)
第406章(第1页)
她默默转过身,舅妈忽又扳着她肩头,小声问:“嘿,你是不是已经有了?刚看着好了些,这几天人又变瘦了,不吃饭,可是溜酸的青疙瘩桃子你又要吃!”
这真是活天冤枉!她猜到舅妈说这话是来诈她,已不愿辩解什么,只苦笑了一下。
艾雪打了热水上楼去,仔细地给他洗手、洗脸,解开上衣,从脖颈擦到了胸前。
她想:“噢,想不到我今生今世还能够这样的抚摸他,亲近他,以前是没有的,这是头一回呀!他在谷风镇住医院时,虽然也昏迷不醒的,也很虚弱,但料理他的是那个护士,我才懒动呢。
“哼,这个千刀万剐的恶棍,我要杀死他才解恨!但是他现在既然掌握在我手中,属于我,我不妨任意摆弄他一会,过会儿这一切都将化为乌有了哇!”
她指尖在他右颊那道长长的伤疤上滑动了很久,然后移到他白皙发亮的隆准上,移到他的红唇上。诧异随着岁月的流逝,他的皮肤变粗糙了,下巴变青了,可嘴唇依然是红红的,未能脱尽女气。
这说明他的心像女人一样毒,哼,都说最毒不过女人心!
她不敢去摸他乌黑的眉和线条清晰的眼睑,担心那样会下意识地抠出他的眼珠子。哼,何必呢,留他个全尸吧!
她开始给他换衣。怎能让他这样脏兮兮的去见上帝呢,这是在她的闺房里呀!
上衣换毕又去解他的裤-带,她心怦怦跳,害怕他这时会醒来——或者他根本就在装,会突然睁眼,那她会羞得无地自容,只好开枪打死自己了!不,是同时打死,噢怎么同时法?
他开始时用手护着腰,不让她解。接着他自己扭动起来,脱下裤子。他的动作使她大为害臊,几乎要背过脸去,幸而他还知羞,从腿上掉下来的只是外裤。她遂上前抱住他,重重地掼在床上。
他一条毛毵毵的长腿搭在床沿,头埋在枕头里,口里又叫:“丫丫!”
艾雪想,丫丫肯定是件悲剧,她死了?她想放声大笑,复又嘲笑自己,你这傻蛋,什么悲剧喜剧,都与你无干了,你就下决心演完自己的戏吧,哈哈!
她怀着激动的心情坐下梳妆。由于手不听使唤,所花的时间多了一倍。镜中女子垂两根小辫,额前覆着刘海。虽然脸蛋黄黄的,眼圈红红的,可微微抿着的嘴角依然带着骄傲与自信。
艾雪端详着镜中人,对她说你虽然又黄又瘦,憔悴不堪,还是漂亮年轻,很有风韵的呀!趁着这样陪他撒手人间,才是值得的呀!你可没有白活呢!
同龄人好多都在农村当知青,过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,你能在城里工作,该享受的你都享受了。唉,唯有一样东西我没有尝过,就是爱情。
这究竟是怎么回事?女人就为爱情存在着嘛,世上生我,一个聪明漂亮的姑娘,却得不到爱情?
啊,今生得不到的,来生将会得到。来生又会有一个他,和一个我,长得一模一样。
啊,反过来让我折磨他吧,反过来让我得到他呀!这位不信神的姑娘,此刻竟极为虔诚地默祷着,在心灵深处向冥冥的上苍呼吁着。
她慢慢又恢复了平静。心如古井水,泛着青白色的光。她打开抽屉取出乌亮的小手枪。床上有响动,从镜中窥见他已经坐了起来。她转身很俐索地举起手枪,毫不犹豫地勾动板机——
“叭”,这颗漂亮的头颅转瞬间血流满面,丑陋不堪。然后她不慌不忙地在梳妆台前坐好,对准自己太阳穴开一枪。这样头上只有一个很隐蔽的小枪眼,亲友告别时见到的艾雪宛然若生……
“砰!”一声骤响,杨灵晃一下跌倒,他脚踢在热水瓶上,倒下时又撞翻了小书架,上面的花瓶、闹钟都滚下来。热水瓶爆炸的碎渣、热水,洒了一楼板。
她听成是手枪响了。把他拖起来,自己坐着,让他靠在膝头上。见他头上并没有淌血,她知道弹孔有时出血极少,遂在头发里仔细寻找,像在捉虱子。
怀里的人扭动起来,哼,他好端端活着,原来枪里没有子弹!
她快速上好子弹。这时外面传来沉重的皮鞋声。
阿果在说,“舅舅”,声音就在门边。
“咦,她屋里在做啥子?”
“哦,我才进去看了,没啥子,是姐姐她……”
艾雪抢着道:“舅舅,我倒开水不小心,热水瓶爆了呗。”
怀里的人醒了,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神情古怪地盯着她。
舅舅又说了些什么,她已没法听清。他突然拉灭了灯,将她紧搂着,使她几乎憋气。
她挣扎着,竭力用平缓的语气对门外说:“舅舅,没事,你、你下去吧!”
舅舅没有立即走,他有可能强行开门。醉鬼竟知趣地安静了片刻。
门外仍无离开的脚步声。醉鬼沉不住气了,毛茸茸的喷着强烈酒气的嘴在她脸上、脖子上不停地摩擦,寻她的嘴唇,她倔强地别过头去,颈项被他咬得痛。
门外仍无响动。她违心地、痛苦地叫道:“舅,你走吧,我都睡了!”
舅舅终于走了。她感到自己已耗尽了力气,像只小羊那样,被他抱上床。她来得及把手枪塞在枕下,紧接着他小山一样的身躯就压下来了,叫她动弹不得。
他使她陷入了恐慌之中,羞辱之中,痛快淋漓的纵欲与解脱之中。她闭上眼睛,放纵自己的躯体让它尽量的舒展啊,放纵自己的心让它尽意的狂跳啊,放纵自己的每一根神经让它们尽情的颤动啊!
后来他拉亮了灯,使她的每一寸肌肤都像含羞草那样颤栗着。这时她心里竟产生了一缕幻想—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