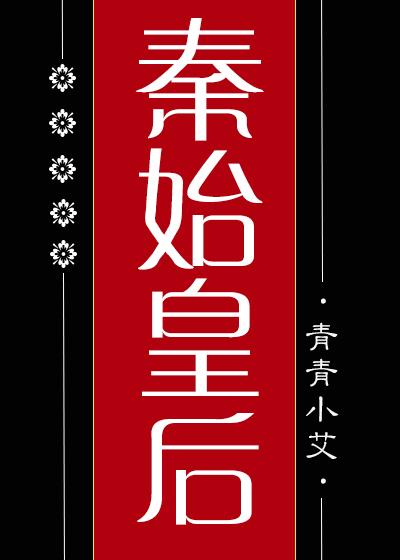千千小说>SD短篇同人(主bl向) > 第85章(第1页)
第85章(第1页)
某天三井去铁男的小铺子找他,忽然想起来,一边翻画一边假装不在意地问:“除了最初遇见时候你给我的那副抽象画,你好像并没再好好画过我。喂,是不是该给我画一幅肖像?”
铁男心说我还不知道你?你想找的那张画我早处理掉了。专会吃醋的家伙,我可惹不起。当然了,为了不惹三井生气,他当然不会说出来,凑到三井耳边笑眯眯问:“只怕你不肯。喜欢什麽样的?现在樱花正好,搭配民族服装如何?”
三井惊讶于铁男的乖顺,停下手审视着那张有些假的笑脸,铁男不呛着说话时候往往在隐藏真正的想法。“我从没听你说过家人,铁男,你一定有……至少有过家人吧?”
铁男愣了一瞬,松快叹了口气,去挑画布了,“有。还有一个异父的妹妹,不过我妈不在了,我不好去打扰人家父女天伦。”
“小你很多?”
铁男在几块画布间举棋不定,“嗯,比你还小些,今年该……”他想了想,“上高中吧。”麻的粗但易定型,帆布质感好但易受潮,涤纶性能最好但缺少肌理感,总之,各有各的优缺点,哪种都配不上三井的完美
——反正他觉得三井完美,他握着一张雨露麻的布角向三井看过去,“你是真想要一幅肖像画吗?”
“你在想这个?也不是,就觉得你不画我一次不应该。”雨露麻是传统画布,久经考验的材质,不完美但不出错——简直不像铁男,但又莫名的很像,粗、坚韧、实用,添图颜色上去,一笔是一笔。“雨露麻很好啊,就这个吧。我不想要樱花,我想要雪景。”用很像铁男的画布画一幅自己,很浪漫吧,三井笑得如阴谋得逞。
“这个季节上哪儿给你找雪景去。”铁男心直口快地反驳,忽又想了想,抓住三井舞过来跟他打闹的手,“也许宗谷岬还有残雪,我也没去过,听说能看见罗斯。”
说走就走,任性如这俩人,彼此不约束,再没人能约束他们。从羽田到稚内要飞2小时,这条线客人少,没有大飞机,小型客机又窄又颠簸,又赶上了航空管制,结果这段旅程比跨国游飞上5、6个小时更累些。一落地三井就开始耍赖,挂在铁男脖子上死活要先找地方睡一会儿。
他们没做计划,铁男琢磨也行,先落脚,他去打听打听附近有什麽吃的玩的。他看三井两只眼窝都凹了,脸色也没光泽,自然心疼,干脆带着他就在机场附近住下。
天气不错,但是冷,风里夹杂寒意,扫过脸颊指缝,比湘南冬天最冷时候更冷三分。铁男裹紧夹克,环视一圈不免有些失望,这个以“最北”为噱头的城市,小而简单,空旷而粗糙。
刚问酒店前台要了一张旅游地图,零散标识的几个旅游景点无非“最北点纪念碑”、“最北的汤泉”、“最北海岬”、“最北之岛”……不用去只看名字也能猜个七七八八,最多形制上的不同,本质上无非为了接待旅行而立的旅行景点,可以说是目的决定论的典範。
铁男在青藏线上跑了两年来的驴友领队,见过太多山峦荒野,对这种人少空旷的小地方兴致不高。特别是这片滨海,不是不喜欢海,是现在每天都能看见海岸线,最北的海并不比湘南的海更美。
两耳灌满来自北方的腥鹹海风,视线里唯一让他欣慰的是确有些残雪,积在茫茫荒原里。至少“雪景”的要求满足了……吧。这点儿髒兮兮的残雪算不得景,枯黄的连天干草上,丑陋得像一块疤。
大概两个多小时后,他租了辆车回到酒店,估计三井该醒了,想叫他吃点什麽,明天随便逛逛,订后天的票趁早回家算了。进屋却还是漆黑的,没有动静,他感觉不对,低声唤到:“三井?还睡呢?”
有一声很低的回应,拉长却没力气的“嗯”。铁男吓了一跳,赶紧打开廊灯,借着这点奶黄灯光,快步走到是床头,从厚厚的被子里刨出三井烧得通红的脸。
“这麽烫!感冒?还有什麽感觉?”铁男握着三井额头慌忙问,心里无比懊悔,是他提议跑到这麽个破地方来的,不但不好玩,还把三井弄病了,他真是笨到要死。
三井拉着铁男刚回来还冻得冰凉的手枕在脸颊上,强打精神笑了笑,“没事,谁还没感冒过。这里好玩吗?看见雪了吗?”
滚烫的脸烫得铁男整颗心都抽抽,他吻上他额头,尽量轻松地劝:“去医院吧?”
“不去。陪我躺会儿,骨头缝疼。”
烧成这样没有不疼的。铁男被三井任性地拉到身旁,觉得怀里简直抱了一盆火炭,烧得他体重里那七成的水开了锅,冒着泡上下翻滚得剩下那三成骨肉不得安生。
他说去买点药先给他吃上,三井嗯嗯啊啊答应却不放手,胳膊腿并用织成网,死死缠着他。他心急,想该绑了他送医院去,又狠不下心,放纵着他再休息一会儿,可又觉得不行,烫成这样总得先退热。他反複纠结着,恨自己遇见三井的事就优柔寡断起来。
三井呼出的气都是烫的,鼻子倒不塞,但只用鼻子气不够用,张着嘴喘得满口干涩,唇都裂了。他拿额头抵住铁男胸口,铁男出汗了,身上凉,抱住很舒服。他往他怀里又钻,忽发现铁男胳膊后背都得绷很紧。他烧得头晕脑胀,合着眼睛实在懒得动,撒手翻平推了铁男一把,“渴,弄点儿水来,要甜的。”
“嗯。”铁男答应了,带着满身汗,跑去给三井买甜的水和退烧药。他身体自由了心里并没跟着轻松,出于运动员的自觉,三井平时几乎不肯喝甜饮料,主动要糖水一定是难受到了想宠爱自己的程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