千千小说>死对头的尽头是…… > 第101章(第1页)
第101章(第1页)
邱明德让人调了监控一看,确实看到他们一唱一和,于是把他们留下了,傅閑能因为打架也必须留下。
张欠没说话,看他一眼,想留下的意思非常明显。
但傅閑能向后递给温朋湖一个眼色,然后扭头一直看着邱明德,颇有无怨无悔的架势。张欠蹙眉,想说点什麽,却被温朋湖和梁其帅拽着离开政教处。
……
傅閑能他爸的消息比互联网传播速度还快,等他被处分完,一出校门,郑哥就开车来接了,说他爸请他回去。
坐在车上,他第一次感觉被处分是多麽无所谓的事,只要想到张欠的成绩保住了就觉得心安,觉得比什麽都重要。
到家后,他爸反而不在,于是傅閑能就自个儿待在他爸的书房,翻看他家公司的历史册,上面记录了大大小小公关危机、经济危机和经营模式变革什麽的——在这个家也就只能拿这些东西来打发时间。
他翻到了2017年。
最大一件事是建酒店时的命案,当时包工头卷钱跑路了,底下工人没拿到钱在闹,有一个领头的爬到27楼的阳台威胁,不慎摔下来当场死了。
本来这事儿有专门的人交涉,却没办好,他和他爸还有安不乱一家只能临时改道去现场。
傅閑能隐约有一些印象,但没有过多了解,所以记不清了。他继续往后翻,看到一张照片忽然愣住。
——印在册子上的是报纸截图,报纸拍了张合照,有他爸,两个陌生男子和战战兢兢的毛女士,以及别着头的男孩。
他再认真看报道的内容,那个领头讨薪的姓张。
看着瘦小张欠站在最边上,那天还是秋天,他只穿了大码白色背心和黑色短裤,贴着毛女士怎麽也不肯看镜头,忽然,傅閑能想起来了那一天。
傅閑能坐车里,还真是一辆库里南,安不乱跟他坐一块,全家和他们一起出国看望他妈。
安不乱向外张望,外面下着雨,一群人在雨幕中着急忙慌处理那件麻烦事,隐隐还听到尖锐的哭声,烦躁地皱眉,说:“穷人的事处理起来最麻烦,这都多久了?快误机了!”
傅閑能从手机上擡眼,没什麽表情,“是吗。”
“那还有假?我看我爸给人塞钱塞女的塞各种卡茅台就能把事儿办了,但穷人给一点甜头就会贪得无厌,纠缠不清,待会你爸要被勒索天价赔偿费了。”
“纠缠不清?……”傅閑能不知道他说的会是什麽场景,稍微倾身看一眼,正好对上三米外的男孩,他穿着白色背心,半身站在雨里,皮肤被雨水沖刷得很白,使得肩上的红痣愈发鲜,深深印在眸里。
男孩很沉默,但他似乎耳尖听到了他们说的话,擡起眼,兇得像炸毛的猫,然而他忽然凝滞了,傅閑能还没明白他为什麽怔住,安不乱就把门关上了,说:“咱们先走吧,不等你爸了。”
之后傅閑能再没见过他,在国外陪他妈治疗的时候也没了解国内那件事怎麽解决的,犹如过眼云烟。
原来死的张欠的父亲。难怪他总是不喜欢欠别人的,对于感情这麽收敛,生怕别人误以为是纠缠不清。
这就是他看不惯自己的原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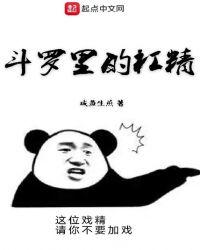
![七日逃生游戏[无限]](/img/31396.jpg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