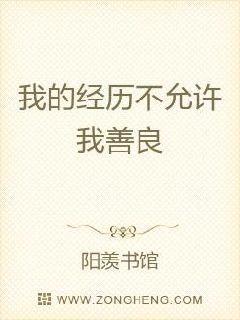千千小说>继室难当,侯门主母重生后摆烂了 > 第580章(第2页)
第580章(第2页)
她不由得浑身哆嗦了一下。
下一瞬楚临渊再次将她捞起,却是迈步上了床榻。
昨日床榻上的瓜果倒是不见了,沈峤躺在床上,下意识地将被扯过来,想要给自己蒙上。
她却不知此时的她,浑身洁白如刚出炉的白瓷,一头青丝似瀑布蜿蜒,大红的锦被上面绣着鸳鸯戏水,一红一白,在这床帐尺寸之间。
却是让人见之便血脉奋腾的存在。
楚临渊喉头微动,忽然停了下来,捞起茶壶斟了一盏茶给自己。
沈峤原本的紧张,顿时松弛了下来。
她紧张的时候,浑身都仿佛煮熟的虾子一般,泛起红润。
楚临渊眼神并不移开,仍是黏着在她身上,却仰头喝了一盏茶。
随即又斟了一碗,缓缓走上前,不过两步,却咚咚似压在了她心上。
“可渴了?”楚临渊递过来茶盏。
沈峤点头,心里想着:算楚临渊这次识相。
随即又有些觉得不对,常言道,黄鼠狼给鸡拜年不安好心。
楚临渊此时分明是已经奔驰到了悬崖的烈马,忽然良心发现勒住了马?
不论是为何,总算不用白日宣银,平白让丫鬟婆子笑话。
白日叫水,她们心知肚明的。
沈峤接过茶盏,仰头咕咚咕咚灌下,常言道女子是水做的。
刚才被楚临渊压在桌子上调戏,她真的浑身出了不少汗,的确失了不少水,渴了。
渴得真切。
她仰头喝了一碗,因为喝得急切,有一滴还掉落出来,滴落在她如玉的身体上。
水滴顽皮地从上滑了下来,滑出了一条曲折的路线,曼妙又唯美。
楚临渊眼底压着欲火,将这一切收入眼底。
却是喑哑着嗓子再次问了一句:“可还要?”